关于我国军民航防相撞问题的反思
详细介绍
熊猫体育军民航防相撞问题是我国军民航之间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民航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而又难以仅靠民航自身得以彻底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民航的发展,同时也给民用航空的广大消费者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如航班延误带来的损失等)。对军航部门来说,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牵制着他们,因此在我国便有了每年一度的“军民航防相撞宣传教育月”活动。民航空管部门更是把军民航可能的相撞列为行业三大风险源之一(另外两个为跑道入侵和‘错、漏、忘’),其定位之高显而易见。如果你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一下“军民航防相撞”,那么约有120万余条的搜索结果(截止2012年2月11日),多么惊人的数字!如果每一条搜索结果都标志着一定社会资源的消耗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耗费的各种社会资源该是多么的巨大!然而,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又是怎么样呢?根据我个人的工作体会判断,答案是十分有限。
军民航防相撞在我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那么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如果有,那么什么时候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深刻反思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而却存在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较大的显著特征。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民用航空运输主要分布在这个地区,同时该地区也是军航飞行量较为集中的地区。近年来,由于军民航飞行量的快速增长,军民航之间对空域和各种保障资源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军民航之间的协调日益复杂,军民航防相撞任务异常繁重,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演进为民用航空不能承受之重,并成为民用航空发展的重要障碍。
军民航相撞可分为空中相撞和地面相撞两种。在我国航空史上,1987年6月16日,在福州义序机场上空发生的空军“歼-7”飞机与民航波音737客机在进近着陆过程中空中相撞,当时空军“歼-7”飞机几乎是骑在民航波音737飞机上,造成“歼-7”飞机机毁人亡、民航波音737飞机受损和部分乘客受伤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军民航空中相撞。1983年9月14日,在桂林奇峰岭机场,一架空军“轰-5”飞机在落地后滑行过程中与另一架离场滑行的民航三叉戟相撞,造成死11人伤25人和两架飞机严重受损的后果,这就是军民航地面相撞。虽然近年来没有发生军民航相撞事件,这是关键保障设备如雷达等监视设备的配备,机载设备的改进(如安装二次雷达应答机和机载防撞系统TCAS),一些军民合用机场分离为纯军用和纯民用机场,以及军民航协调工作的加强的原因。军民航相撞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军民航飞行量的增量将逐渐抵销这些原因所产生的防相撞效果,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寻找有效解决办法,军民航相撞将难以避免。
回顾世界航空发展的历史,早期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定性为“技术时代”,当时安全关键问题大部分与技术因素相关。航空当时正在作为一种公共交通业兴起,而保障其运行的技术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技术故障”乃是反复出现安全事故的因素。安全努力的侧重点当然放在了调查及技术因素的改进上。
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重大技术进步,开始使用喷气式发动机、雷达(机载和地基)、自动驾驶仪、飞行指引仪,完善了机载和地面导航与通信能力及类似的性能提升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减少了“技术因素”导致的安全事故,但是随着航空运输的飞速发展,安全事故总量并没有减少,另一个“人为因素”的主要致错原因浮出水面。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被称为航空“人为因素”的“黄金时代”应运而生,这也预示着“人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机组资源管理(CRM)、航线飞行训练(LOFT)、以人为中心的自动化和其他人的行为能力干预措施开始不断涌现。
在“黄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为因素”方面的努力的消极面是这些努力倾向于着眼于个人,而很少注意个人完成其使命所处的运行环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才首次承认个人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在一个限定的运行环境中作业。这标志着“组织时代”的开始,即开始从系统化的视角审视安全,并从而涵盖“组织因素”、“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
对照一下我们所进行的军民航防相撞活动,基本仍停留在“技术因素”,或者“人为因素”时代阶段,这也是其效果有限而不得不年年开展,时时讨论的原因所在。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从“组织因素”的角度,即从军民航矛盾所存在的系统环境,如国家政策、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军民航防相撞问题的剖析,实践将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难题,这一点正是军民航防相撞问题的正解。
军民航防相撞的做法目前在我国主要采取军民航运行单位之间在基于双方协议约束下的即时协调,军民航临时互派联络员,以及军民航防相撞宣传、教育和研讨等方式实施。这些方法在军民航飞行量较小,军民航飞行量增速较慢,以及跨区域活动或限制较少的情况下还可以满足实际需求,但是在军民航飞行量较大,而增长又异常迅速,以及跨区域活动或限制较多的情况下,将无法适应实际运行需求。后者正是我国目前的现状,这种不匹配在我国的直接体现为军民航相撞风险日益增大和为控制这种风险而采取的流量控制措施,而体现在用户层面就是航班延误几率的增加和航班延误幅度的扩大,从而造成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各种社会成本迅速增大,并逐渐将航班延误问题演进为社会焦点问题。
随着空中交通的不断发展,空域资源相对空中交通需求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的航空运输量还远远小于航空发达国家,但空域资源紧张问题已十分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空域资源的稀缺是相对的。从地域角度分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宽裕的空域资源,当然西部高原地区由于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空域资源的可用性存在一定程度不可操作性,但扣除这个因素仍可反映出我国空域资源稀缺的相对性。绝大多数军民航飞行集中于东部地区,这个地区不堪拥挤的空域状况成为军民航飞行矛盾的主要原因,防相撞之难显而易见。
我国的空域政策仍沿用建国初期民航规模较小,所需空域有限,空域由空军负责管理使用的国家政策,虽然近年来移交了几条航路给民航,但是整个空域政策框架没有实质改变。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民用航空飞行量已经具备中等规模,并继续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现行国家政策已经严重无法适应发展的航空运输的迫切需求。这些不适应主要体现在:
(1)空域管理仍处于战略层面管理粗放,预战术和战术层面协调机制不够顺畅,军航使用块状空域的自主性较强,而且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静态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新辟航路、航线,或者航路航线结构优化难度巨大,另一个后果是往往造成民航部分航段高度“卡死”问题,第三个后果是主观随意性较大,协调效率低,这些已经严重不适应高流量的迫切需求。
(2)军航飞行通常在昼间目视气象条件下进行,空域资源闲置时段较多。民用飞行通常实施全天候仪表飞行,但却仅限于航路、航线和机场附近空域。空域资源难以实现共享,浪费严重。
军航和民航作为在同一空域内运行的两大主体,但其法规标准却各成体系,而且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
(1)运行标准方面,民航基本上为精密仪表飞行,而军航通常仍停留在穿云航线等非精密仪表,或者目视飞行阶段。
(2)间隔标准方面,民航通常为雷达间隔,或者雷达监控下缩小间隔,而军航间隔却要大得多,甚至通常还采用程序间隔,在垂直间隔方面也比民航大一倍或以上。
(3)差错标准方面,民航使用明确的《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行业标准,而军航却缺乏明确的差错标准。
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使得在同一空域运行的军民航之间协调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其协调之难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却仍然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和谐”地协调着。
军航管制部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获取更多直接的军民航飞行动态信息,而民航管制部门对军航飞行动态的信息掌握却极为有限,因为军航飞行往往不开二次雷达应答机,民航雷达无法扫描并显示,仅靠军航管制部门的通报协调,是无法直接、全面掌握其准确信息的。这样的状况对民航管制部门来说充满了茫然和无奈,军民航协调危机重重,安全隐患层出不穷,防相撞任务异常艰巨。
军航管制人员通常不直接对空指挥,一般充当了协调员的角色,而且没有民航管制经验,不具备对空指挥能力,一旦出现应急情况,往往丧失最佳处置时机,而民航管制人员却恰恰相反。人的因素的巨大差异往往导致在防相撞问题处置上的不同步、不协调,军民航冲突孕育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以上四个方面充分说明,在我国军民航防相撞问题解决的难度远比人们能够想象的要困难,因为解决无论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都会涉及到更多的其它方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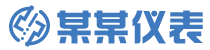
 扫描进入手机站
扫描进入手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