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在照护妻子的那些年我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2024年已过近半。在上半年的公共讨论中,“照护”再度成为话题的焦点。《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引发网民热议,胡泳自述照护85岁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故事触动着很多人。那篇文章最后,胡泳感慨:“照护与被照护,这两个身份你永远逃不掉。所以你越早思考这个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事,对你来讲更有益。”
哈佛大学教授凯博文是最早将“照护”引入公众视野的学者之一。在妻子琼被诊断出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病后,凯博文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照护者”生活。他将这段经历写入《照护》一书,在中文世界同样引发共鸣。日前,凯博文带着他的“照护”研究来到中国。
6月24日晚,凯博文与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潘天舒、《照护》一书的译者姚灏、作家于是一道,共同探讨了“照护”在当代的重要性和困境。时隔多年,凯博文再次谈起照护妻子的过往仍旧动容。他说,他和妻子结婚46年。在这46年的婚姻中,前36年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他,然后他照顾了她10年。“我觉得对她提供10年的照顾,甚至不能够平衡我们之间这种相互依持的关系。”在凯博文看来,“照护”本身对于照护者来说也同样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成为更好的人。“而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要到这个世界上去为别人做事,你才能找到自己是谁。”
在活动后,凯博文就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关“2024日常出逃计划”的问题,即每个人作为自己的第一照顾者,如何在当下倍感压力,忙碌、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这一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于是:为什么“照护”以及“正确地理解照护”,是非常重要的?《照护》这本书对于您的学术和写作生涯来说,是否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凯博文:照护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胶水”,它让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都能凝聚在一起。我对于个人关照和照护的理解,受到了我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做调研以及认识的很多中国人的影响。
照护的重点在于人情关系。对我来说,人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和道德连接。为什么道德感在里面?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最重要的。所以照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照护有道德和情感的关系在里面,它原初是家庭关系。而问题就是当我们寻求系统性的照护的时候,我们会去到像医院和诊所这样的地方,寻求专业性的照护,它的性质就开始不一样。
在医疗系统下,医患关系问题如今在全世界都显著存在。这是因为在我们“关照的关系”中存在着系统性,比如说对于医院这样的体系,他们更在乎效率是不是更高,甚于照护关系的质量。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当我的妻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我开始从我的朋友们那里寻求帮助,他们都是哈佛医学院很优秀的医生,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而是从医生的角度,给我们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作为医生,他们想要在很早的阶段就作出诊断,而由于阿尔茨海默病是没有可以治愈的方法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提供太多治疗,而是让我很早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其实对于医生来说,他还是有很多建议可以给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的,但我那些优秀的神经学科的医生朋友对此一点儿都不了解,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接下来的10年,我要照护一个患者,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一直保持在场,一直作为一个有爱的丈夫存在于她的生活。医生们不觉得这是跟医疗相关的建议,但事实上,这些才是在医疗系统和医患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建议。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持续衰退性的、严重的神经性疾病,尤其是当它影响到整个衰老人群的时候,我们就试图通过这些疾病去看看我们的医疗体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另一个我想通过这本书分享的是,在具体的照护中,你要怎样做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力传递给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不纯粹是一个负担?必须承认这很难,但是我们从中也能够找到意义感。
我和妻子已经结婚46年。在这46年的婚姻中,前36年都是我的妻子在照顾我,然后我照顾了她10年,我觉得对她提供10年的照顾,甚至不能够平衡我们之间这种相互依持的关系。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10年的照护如何让我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并且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到底哪里出了错。
于是:为什么要把医学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潘天舒教授创建了复旦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学科,我觉得由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再好不过了。
潘天舒:我就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下。我最早看到《照护》这本书是在疫情之前,当时我去美国访问,在凯博文教授的办公室里,大家看我朋友圈也看得到,那时已经有样书了,大概是2019年的8月。熟悉凯博文教授作品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在很早的时候,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就显示出一个很不安分的医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形象。他写的论文非常有意思,在《医学的符号现实》(《the symbolic reality of medicine》)这篇论文中,就已经开始质疑西方的这个制度了。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多地在两个领域里开始做这个事情。
《照护》这本书预示着他成为了一个照护者。2007年,他带着他太太进行国际旅行,一般人是不敢在阿尔茨海默病到这个阶段还这样做的。我记得当时看到他跟琼说西班牙的画。虽然琼因为生病,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但我注意到,当凯博文在解释时,她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我觉得她的记忆又被唤起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把灾难性的事件转化成了进一步学术探索的机会、契机,而这些学术探索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早就出现了。如果你去看《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愈疗者》),那本书吸引了很多医生走上医学人类学的道路。当时他已经谈到了照护的系统,这是他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一次田野经历,后来他又写了《崇思精神病学》,有时候也被翻译成《谈痛说病》。在照护期间,凯博文在《柳叶刀》大概发表了20篇文章,都是专门写Care(照护)的。
于是:在《照护》一书中,凯博文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四大医学悖论。一是照护在医生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二是在照护这件事上,医生可能比护士做得更少,但是他们其实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三是医学院的新生更愿意投入到照护的实践中去;四是技术本来应该是为了减少诊断和治疗的差错,但却削弱了照护。
作为一个持续关注照护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照护者,请问凯博文教授,您觉得现在这些悖论有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在全球的医疗卫生环境中,照护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与实践?
凯博文:有一些改进应该是在发生的。在美国住培医生的培训体系里,一年级的医学生其实比四年级的医学生对患者的照护要更好。这说明在住培医生的培训里,有一些培训方式其实让医生的照护技术变得更差了。当然,也有一些切实的改进。比如,很多学校会给医学生增设人文和社科类课程,但我们都知道这非常有限,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与工作异化产生的结果。
美国的医疗系统和中国非常不同,但是我们共享一些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在医疗体系中,患者并不被当作是医疗体系的中心。以前医生被当作医疗体系的中心,现在医生也不是了,而是这个系统本身。追求系统的高效能化,取代了患者中心的医疗模式。
那么,什么叫做“系统的高效能化”?就是说一切都被数据化了,我们这所医院以什么样的速度诊疗、有多少病人通过就诊,然后达到了怎样一个结果,花掉了多少成本,这种经济学的语言体系已经入侵到了每一个系统当中。如果系统的高效能化已经成为中心,我并不是说我不希望一个系统变得效率更高,而是有比高效能更加重要的核心,比如说照护。而作为医疗系统,照护本来就应该是医疗系统的核心内容。
在场所有人可能都体验过这种高效能、但无关照的系统带来的问题。照护的关键在于花时间。我曾经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但再优秀的医生也不可能在5分钟之内看诊病人,并且提供照护。所以,我们需要整个体系的转换,需要把高效能变成以照护为中心的医疗系统。我们衡量患者痊愈的结果,也不应该只是经济上的结果,而是对于患者整个人、整个人生的福祉。科技和技术应该是为照护本身而服务的。
在这方面,对于像阿尔茨海默及其他神经衰弱型的症状和疾病,就更加重要。我们的社会在进一步老龄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用到这样的服务体系。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比美国要更好。在中国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长期护理保险,而美国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开始的。
于是:接下来这个问题要问潘天舒教授。之前我听您提到过,你们一直在做适老科技的调查和一些社会工作。潘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国内的适老科技有什么样的改变?
潘天舒:好吧,我就说一些我知道的事儿。这一切是从2017年开始的。2017年3月,在江苏产研院,凯博文老师带来了横跨哈佛7个专业的一个团队,来谈如何设计老人的福祉。他当时用了一个非常现代未来主义的词Exoskeleton(外骨骼),就是穿戴机器人。然后他提到,在照护琼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是希望有这样一种技术的,但在2011年还没有。
他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有多厉害,事实上他是想表达,正是这个技术的出现才能够让他继续扮演琼的主要照护者的角色,能够使他照护的道德体验得以完整。如果它能成为一个现实,还需要它是一种大家都能买得起或者租得起的技术。
熊猫体育
这里面,有一个“社会科技”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和凯博文老师之前提过的所有概念相比,“社会科技”大概是最清晰的。这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首先要做到跨学科,而且要做到公正、普惠,不是只有精英老人才用得起的科技。当时参会的还有哈佛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他说他要求学生在设计中风老人的衣服时,要考虑普通的老人是不是能买得起。
我们也在做一些事情,其中有4年我们办了暑校。暑校实际上是受到了凯博文老师和陈宏图教授在哈佛教的一门非常特殊的课程的启发。大概哈佛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门课,跨了7个专业,也就是把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全部打通,所有的学生都是修课,不打分,学生只有“通过”或“不通过”两种结果。毕竟拿分数不是最主要的。这些学生在修课期间,到了假期会来中国,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做一些实地调研,而他们可能是来自商学、医学、公共卫生、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学生。受到这样一门课程的鼓舞,我就和我们学院的陈红林老师(现在他到芬兰去教课了)从2018年开始到2021年,连续四年在复旦研究生院开设了“适老社会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课程。其中有两次,于是老师作为嘉宾来讲了课。
于是:我个人觉得照护像一个最大公约数。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像潘老师说的,它能够把各个学科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人在照顾自己的家人、甚至是照顾邻居。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一定会下意识地用上自己的专业知识。比如一个设计AI的科学家,他一定会去想怎么样能够减轻护工的负担。我想起给我父亲找养老院的经历,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不是很容易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照护的机构。当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排队。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床位,而是因为缺少人手。我就想,如果我是一个造机器人的工厂,我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请我们的翻译——姚灏博士解答。您是在一线做临床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翻译这本书后,对于我们上述聊到的问题您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以及中国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
姚灏:其实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当时我正好在国内做了两年住院医生,然后Gap(休息)了一年,出去读了一年书。所以,当时我也处在一种非常好奇的状态。刚刚凯博文教授也谈到,医生其实是非常容易好奇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知道,国内做医生确实工作量很大,像我们出门诊的线多号病人,一个病人只能分到5分钟左右。因为你一旦给某一个病人的时间过长,可能后面的病人就会有一些怨言。
我们现在整个医疗体系非常注重效率。医院里我们讲一个词叫“周转率”,也就是病人平均住院多长时间能出院。如果周转率降低,整个卫生经济成本都会上涨。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其实不光是病人,医生的“人”的成分也在消失。医生也像一个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在不断地去修复一个又一个的“零件”。我们也很希望提供更多人性的关怀,但是一些体制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摆在那儿,所以很难做到。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心内科时,有个病人来做房颤手术,进一步检查后,我们发现这个病人是有肺癌病史的,通常肺癌晚期病人的很多指标都会处于异常状态,按理说他并不适合做房颤手术。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我的任务就是把房颤给治好。如果说,这个病人不符合我做手术的适应症,指标不太好,那么就没有办法,到这里,我的任务其实就结束了,但是这样真的合适吗?
现在医疗技术发展很快,但我们的医疗教育还是围绕技术本身去展开的。比如,报告怎么读,X光片怎么拍,之后怎么看片子,都是围绕这些。我们在医学院里的教育不是去关心这个病人,而是关心我们怎么上解剖课或者病理课,怎么去看一些标本,看人体的一些不同的部位或者看显微镜。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治病救人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下,对于一个病人个人的情况,疾病背后的故事,具体究竟有多痛……我们是听不到的。整个医学教育就只是在讲人体的部分,但关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是非常缺乏的。
于是:姚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应该增加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听了之后,肯定焦虑感又上升了。如今老龄化的进程在持续加快,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老师给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支支招。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够让照护和养老变得更人性化?
凯博文:我对于整个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希望大家也能保持乐观。在各个国家,居家养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政府应该提供给每一个家庭相当多的资源,不一定只是经济资源,知识资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对于老人的照护都是从零开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有挑战,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方式来分享资源,大家就不会那么局促。
同时,随着适老科技的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永远应该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人服务于技术。此外,我们所有人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都是去入世、做事、助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这在中国是很古老的智慧,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新的看法。现在美国流行的心理学,都是让大家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然后去诚实地表达出来,但其实要成为一个人,必须要到这个世界上去为别人做事,你才能找到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其实照护本身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因为照护强调爱,强调家庭,强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在照护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习得如何做人。
读者:凯博文教授,您好。您曾经做过外科医生,后来从外科医生转向精神科医生。这种转变是为什么?
凯博文:1960年代,我最开始从医时,并不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是一个治疗传染病的医生。当年我治疗的大部分疾病类似于肺结核和霍乱。我从一个传染科医生转型到精神科,是因为我对疾痛的社会性非常感兴趣。而那个时候,精神科看上去是对这方面最重视的一个科室,而现在一切又转变了。比如,现在精神科更专注于生物医学方面,而内科却更注重社会性。
我一开始对这些的兴趣,来自于我对慢性病的治疗。无论是糖尿病、心脏病还是癌症,当你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尤其是长期与患者相处时,疾痛经历的社会性和他们的心理状况会浮出水面。
读者:我是从事一线工作的护理员,专门照顾老年人的。我现在也在做认知障碍方面的培训和照顾。刚才于是老师提到,为什么养老机构不收这些认知障碍的老人,是因为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会出现很多风险,出了问题的话,家属会找我们赔钱。我想问的是,一线医护人员在照护认知障碍的老人时,其实心理压力很大,我们该怎样去舒缓这方面的压力?
凯博文:首先因为您本来就是一个照顾老年患者的人,所以您有自己的经验。另外,近些年,在照护方面有了一些技术上的增进,比如说设置摄像头系统,这可以减轻护工的很多工作,如果有人一不小心走出去了,我们是可以从监控系统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技术很有意思。比如,现在我们会给患者提供一些VR(虚拟现实技术)的、由人工智能操作的智能眼镜,在里面可以放一些影像资料,能够让老人们在情绪激动时安静下来。
在人力资源安排方面,应该提高护工、护士和社工的社会地位。在美国,当护士的地位和护士的工资都随之上涨的时候,护士的训练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也会相应提升,他们受到的尊重也会更多。这样,社工分担的具体照护工作也会更全面。比如在美国,很多时候心理咨询不是由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医生提供的,而是由社工提供,因为心理咨询师提供的心理咨询有点太贵了,很多患者承受不起。由社工提供的话,就更普遍、更全面,而且患者也更容易承受。此外,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设立一些新岗位,比如说健康助理。如今在很多国家,健康助理都被作为一种初级护工,而如果健康助理的社会地位、工资和训练都有提升的话,其实对整个体系是有优化的。
最后就是护理院的整体优化。昨天,我在潘天舒教授的介绍下,参观了一个很好的护理院。那个护理院有很多活动空间,病人的自主行为能力也很强,也有很多非常投入的员工。我的妻子在她人生的最后9个月,是在一个护理院度过的,那个护理院也非常好,所以在那里我深受触动。我认为新模式的引进在各个国家都可以实现,在上海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了。
202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年度活动主题“2024日常出逃计划”——我们期待在不同的话题下,与创作者共同去探讨,如何借由阅读与创作获得超脱性的发现时刻。在此次活动后,我们也请凯博文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书里“尾声”部分,您提到,“照顾他人其实也是照顾自己”,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似乎“照顾自己”变得特别重要,人处于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脆弱平衡之中,被要求更高的工作效率,也越来越被异化为一个“工具”,患有抑郁症的概率大幅增加,所以,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微出逃”,给自己一段时间,脱离现在的生活,哪怕只是短暂的Gap Day(间隔日),也期待在彻底的逃离过后重新获得力量投入日常,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对于处于这样现状中的年轻人,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您有什么建议?
凯博文:我对“照顾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认为“照顾自己”的基础是深入自己的内心,向内找到真正的自我并表达出来。当你审视自己的时候,你会很困惑,一个人内心所具备的感知、情绪和价值观等,是非常混乱且令人困惑的。我认为我们是通过向外走进这个世界,通过努力帮助别人来找到自我的。我认为人是在照护中,从关心他人中找到自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它会强化你的自我认知,让你找到生活的目标。当你向外探索的时候,它会帮你发现自己。
这是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不是通过向内,而是通过向外——照护我的妻子、关爱他人、照顾我的母亲等,来找到生活的目标。是这些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也一样。我们需要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那么自私,要意识到如果凡事都以个人利益为先,你就会以个体问题告终。你需要走进外面的世界去与人交往、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工作,并进行思考,与这个世界互动,通过这些来发现你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生活的目标,知道自己是谁、想做什么。这些构成了“自我”,建立了“自我”。
这并不是我原创的想法,这是孔子和新儒家的经典思想——通过建构自己周遭的世界来建构自我。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花越多的时间审视内心,不仅会越来越困惑,也无法去做一些能真正让我们厘清生活以及更有道德感的事情。

熊猫体育(china)官方仪表阀门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88号
电话:400-123-4567
邮箱:lie12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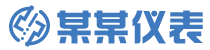
 扫描进入手机站
扫描进入手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