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王颂:汉译佛典中名相翻译的思想文化背景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的王颂先生的这篇论坛发言,主要围绕佛教名相的翻译问题展开。名相,特指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抽象哲学概念在理解上需要有一个很强的思想文化的背景,不能简单用“格义”的观点来囊括这个问题。抽象的哲学概念,不得不借用本有的语言、文化来加以解释和定义,就是说有前理解、前见。前见是普遍的,但前见不等于格义,是用固有的字词进行组合或者重新定义,搭造、生发出一种新的意义来,但是这个字词又和原有的含义有内在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知识考古的研究,把这种隐含的勾连揭示出来,更深入地考察出中国人在翻译佛教名相时所进行的思考,以及两种思想和文化间的内在联系。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谢谢《文史哲》杂志社的邀请。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议。
我谈的话题是关于佛教名相的翻译问题。主旨是什么意思呢?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学者们都提到佛教汉译应该说是人类文化迁移史上的壮举、一个大工程,积累了很多经验。既往的研究多是从历史学等角度出发,一会儿我们看到几位同仁应该也都是从这些角度讲,包括译场的制度、翻译的特色等等。我这个研究角度稍微有些不同,专谈佛教的名相。这里的“名相”,是从狭义上说,特指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关于哲学范畴的翻译,实际上大量沿用了佛教的翻译,比如说“意识”、“世界”、“意志”等等。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中,一些简单的或者说我们日常接触的事物,它的对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说“拿一杯水”,翻译成英文,或者是梵语翻译成中文,问题不是很大,不会有理解的障碍。但是抽象哲学概念在理解上需要有一个很强的思想文化的背景,但这个又不能简单用“格义”的观点来囊括这个问题,或者说简单地一概而论。
关于格义,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章。我们知道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格义。就狭义的格义而言,我们如果考察历史,应该说格义不构成当时的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翻译的方法。陈(寅恪)先生当然很了不起,他写了这篇文章,应该说发古人千载未发之覆了,他实际上是“发明”了“格义”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我进行考证以后,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格义在当时已经是大家公认的或者是熟知的一种方法。但这个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广义的格义而言,陈先生这个观点和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广义的格义作为文化迁移史上的一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就是说,我们理解外来文化时,我们不得不用自己原有的一些东西去理解它,是一种比附,甚至有可能是张冠李戴,是不究竟的理解。比如刚才说到的以道家的“无”来理解佛教的“空”等等。以“无”来理解“空”的这种格义方法,是在思想文化没有深入的、充分的接触和交锋下实现的,它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格义”不免带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大家用这个词的时候,很多时候也都隐含有批评的态度。
而我这里要说的问题,不属于格义。我们翻译和介绍一种全新的概念时,这里指抽象的哲学概念,像上面说的,不是指日常事物,不得不借用本有的语言、文化来加以解释和定义,就是说有前理解、前见。前见是普遍的,但前见不等于格义,格义有个英文翻译叫做matching meanings/concepts,就是把一个外来概念生搬硬套为某个原有概念,我们这里谈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如何用固有的字词进行组合或者重新定义,搭造、生发出一种新的意义来,但是这个字词又和原有的含义有内在的联系。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进行了联想,巧妙地将二者勾连起来,但是并没有明确地把它展露出来。词语可能是借用的,或者是借用加改造的,但在借用以及其后使用的过程中把原有的意思抛弃掉了,成为了新的词汇。这个反而是翻译和文化介绍传播中更为常见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知识考古的研究了,我们把这种隐含的勾连揭示出来,反而能更深入地考察出中国人在翻译佛教名相时所进行的思考,两种思想和文化间的内在联系。这里面自有妙趣,但与格义是不一样的,请大家体会。
我可以找出很多例子,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要通过这些例子来探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但这里限于时间就不展开,只举其中的一个小例子来加以说明,就是“取”和“得”。梵语是upādāna和prāpti。这两个词在佛教学说中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比如说十二缘起里面就有“取”,“不相应行法”中有“得”与“非得”。而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是没有这两个范畴的,一会儿我会解释这两个范畴在佛教哲学里面的意思。那么怎么去翻译这两个范畴?通过研究,我认为翻译者很可能受到了《庄子》尤其是郭象注的启发,所以用了这两个汉字,因为这两个汉字在《庄子》特别是《齐物论》与郭象的注里已经具有了很深刻的哲学内涵,已经超出了日常用语里面常用的动词比如说“取”与“得”的意思了,所以我认为它有一定的关联性。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自取”,这个“取”到底什么意思?“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我查了很多注释,对这个“取”字往往一带而过,没有特别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说万物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都是自然而然的,并没有一个主导者,也就是怒者,来造成这个声音,所以说是“咸其自取”。但是这个“取”确切而言是什么意思?并没有太多人关注。
我们再看“得”,比如说“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得”与“不得”。这个“得”与“不得”构成了一对,这里已经具有概念的萌芽了。后面一个用例就更明显了,就是讨论“无穷”的这段话,“彼是莫得其偶”。更重要的是第二段,关于“寓诸庸”的问题,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里的“得”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名词性的字。郭象对此有注释,我们往下看。其他的用法不说了,我这里(PPT)举了很多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得”和“取”在《庄子》里面是反复出现的常见的词。
大家肯定会问了,在其它先秦典籍里面也有这两个字,为什么我一定要联系到《庄子》和郭象呢?我是有论证逻辑的。我们先看“取”与“得”在汉语里的基本含义。这个在《说文》等典籍里面都有,时间关系,也不用展开讲。那么它们作为普通动词,获取、得到等等,在汉译佛经里面也使用,比如取人财物、取水,在早期汉译佛典里就有的,例子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取”和“得”还可以互训,从意象上来讲“取”是由内向外的抓取,那么进一步抽象化就是“能、所取”,就是“能取”和“所取”。这是认识性的“取”,也包括意愿、欲求的“取”,十二因缘里的“取支”就是这个层面的含义,是对外境的执着。而“得”从意象上来讲是由外向内。这里有意思的是,“得”与“非得”这组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固定翻译成“得”,有的时候翻译成“成”。为什么后来固定了?这里面就有问题,我们就感到好奇,要进行研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不相应行法的“得”并不是一种一般意义的获得,“得”代表凡圣界别性质的转变,也就是说“得”在佛教哲学中特指解脱、成圣,不是泛泛的get、obtain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南北朝的时候,陈真谛已经把“得”用做固定概念了,“得有二者”等等。到唐玄奘的时候,就是有得、非得与同分、无想等都是不相应行法的固定名相翻译。
前人只有章太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用的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向格义”的方法。他说《齐物论》里面“非我无所取,咸其自取”的“取”,就是佛教里面“取”这个名相,他说“似能所取,似所取相、能取相”等等,所以他解释“非我无所取”为没有我就没有我所认知、创造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他运用佛教哲学去重新诠释《庄子》了,他这么说肯定并非庄子的本意。但这倒也给予了我们一种启示,或者说有助于我们的猜想,翻译佛典的人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庄子》里面的“取”?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你看郭象注讲的就很清楚了,他说“厉与西施,恢诡谲怪”等等,“道通为一”,所以说“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性”是郭象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性分”,“适性逍遥”的命题。“性”和“得”有联系。下面讲“用”他也说“自用者,莫不条畅而自得也”。这个“自得”或“得”与“性”一样,都是他引申的哲学概念,与我们日常作为一般动词的“得”是不一样的。成玄英他们沿用了这个概念,说“逍遥者,盖是放旷自得之名也”,陆德明说“怡适自得”等等。小结一下,在郭象那里,“取”与“得”有时是互训的,他曾经说“咸其自取”可以训为“自得”。这些先放下,至少可以看出,它们已经从一般意义上作为动词的取得、禀受转变为与“性分”相关联的状态与境界。
如果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证明佛教徒意识到了可以借用《庄子》和郭象。我们还有一个思想关联的证明,考察他们运思的方式。简单而言,“得”与“非得”本身有一个逻辑关系,而这个逻辑关系是和《齐物论》里面讲的“莫得其偶”,也就是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这个无穷论证是有联系的,就是会产生不断否定的递推,产生无穷倒退的逻辑悖谬。就此我写了一篇单独的文章,讨论无穷倒退——《庄子》称为无穷过——的逻辑问题以及佛教哲学对这个逻辑问题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参考,这里就不展开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证明,郭象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莫若无心”,被南北朝的一位重要僧人昙迁完全借用了。他作了一篇《亡是非论》,其中完全因袭了郭象的说法,如说“将欲不累,莫若无心”等等。这篇文章的全文虽然已经散佚,但这个部分被初唐的智俨引用在自己著作里,同时用来说明“得”的“无穷过”问题。这肯定就不是偶然了。至少说明佛教徒是肯定意识到“得”与“非得”的逻辑关系与《庄子》和郭象注有关联了。这是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明。因此我的结论就是,“取”和“得”是印度佛教特有的哲学概念,理解这个概念比较复杂,因此翻译的人当初找了很多可以匹配的汉字,那么在魏晋庄学流行的时代,他们很可能在郭象注里发现了“取”、“得”这些已经具有特定内涵的抽象概念,同时他们还有大家熟悉的一般语义,于是就用这些词汇去翻译佛教的特定概念了。
回到我一开始说的话,这类具有前见的翻译并不能用“格义”笼统而论,前见没有影响翻译的准确,反而生发出了创新性,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结合。这就好比我们今天说“意识”“意志”“境界”这些词,已经忘记了汉译佛典中它们的本义了,但你决不能说它们二者之间毫无联系。这种联系是隐含的,草蛇灰线,但并非没有,也未曾彻底断裂,这就是我们研究翻译史,其实也就是理解思想文化迁移史所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熊猫体育

熊猫体育(china)官方仪表阀门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88号
电话:400-123-4567
邮箱:lie12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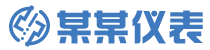
 扫描进入手机站
扫描进入手机站